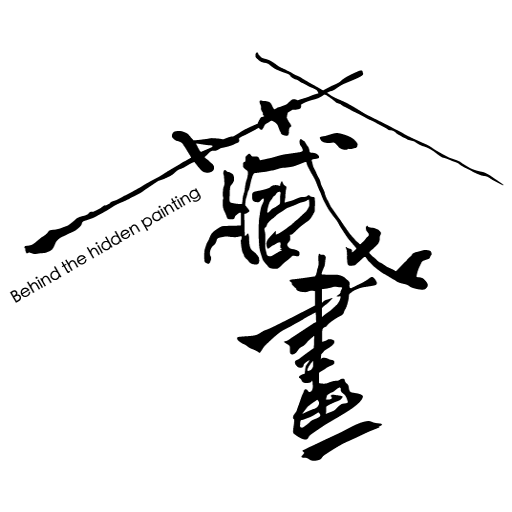文/林文尹
20230306
如芳、佩玉:
這個演員的請教同時寄給編劇如芳以及導演佩玉。
首先我並不希望這個會造成你們的困擾,而在前幾天收到編劇的問題表格時,我其實腦中一片空白,不知道該問些什麼才好。對我來說身為一個演員,我是說對我來說,身為一個演員我應該要做的事情,就是把劇中的人物再一次活出來,再一次地,用他的生命說出他的事情。
當我接到這個劇本,得知我要演的角色(方慶綿)的時候,一如往常的我在想像我要如何去扮演這個角色,如何再一次的讓這個生命站在舞臺上。所以對我來說,如何在舞臺上展現出曾經有著生命,無論是虛構的或是真實的,都是我最重要的工作。
我在接到這個劇本之前對於白色恐怖、228事件都有所接觸,而且也都有演過相關的作品;有很多是虛構的,但那些虛構,建築在許多的歷史文件上,比方說判決書、比方說照片、比方說演出的場地,那些受難者曾經被囚禁的地方。
而這個製作在拿到劇本時,我才接觸到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名字:方慶綿。
接著我用我的微薄之力去搜尋了這個人,但我搜尋到的,就是一些展覽,以及不到1000字對於這個人的描述,描述當中,都是在敘述他的技巧,以及他如何拍攝玉山的景象。而當我開始意識到我要扮演這個人的時候,我的演員直覺,以及我一直以來的站在舞臺上的概念,是我要怎麼幫這個人說話,或者是說我要如何扮演這個人。
而「扮演」這件事情,在舞臺上從來不只是一個演員能夠想像多少來做為依靠的依據。對我來說,需要更多資訊才能夠不愧的告訴自己「我是這個人」地站在舞臺上。於是當我接到這個劇本,一開始讀過這個劇本,明白了我要接觸的這個角色之後,我試圖去查閱這個真實存在而不是虛構的人物,他到底是什麼人?
我必須說,在接到這個劇本之前,我因為某些原因接觸到陳澄波最後的照片,也從中知道那是他的妻子地做為所拍攝下來的,但是我從來沒想過到底是誰拍下這張照片。
直到我接觸到了這個劇本,我才大膽的推敲出「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那個方慶綿?」
當然,這都是歷史上的一個未證實,無論在劇本或是在查閱的資料當中,都沒有一個正確答案到底哪張照片是誰拍的。我不敢猜測也不清楚這個劇本的田野調查是不是有答案?
但是對於當初我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,我非常的佩服那位妻子,甚至每次想到我都淚流不止。因為會有哪個伴侶、哪個你那麼親近的人身體上有那麼多的槍孔,而卻有勇氣地,讓他變成一張照片。
到了這裡我無法克制自己流下眼淚,也從來無法克制自己多麼敬佩那位伴侶,尤其是在那個年代我們所謂的女性,那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勇氣?那到底是多大的愛?那到底是一對怎麼樣的夫妻?去支持起一個浪蕩、一個反傳統、一個莫名其妙的死亡。
一個怎麼樣的人會用這種方式,把自己的另一半用歷史的方式記錄下來?一個怎麼樣的女子,或說是一個怎麼樣的伴侶才有這麼大的愛,去支持他的另一半想做的事情,而在他莫名其妙地被槍殺之後拍了這張照片?
我想說的是,在我看到那張屍體的照片的時候,我從來沒想過是誰拍了這張照片,這個劇本給了我一絲啟發,而我居然要扮演那絲線索!
閱讀了這個劇本之後,我得到了一首歌,剛好是我另外一個製作注意到的〈春之佐保姬〉。我抓住這首歌想要更認識所有的一切,但是那彷彿都是徒勞,因為在study的過程當中,這首曲子隨手可見,而且有很多版本。但是到底是誰拍了那張照片?誰有那麼大的勇氣,在那個時代去拍一個「反叛者」的照片?
我在劇本裡面試圖想要去詮釋這個角色,或說我想要去詮釋這個人、他的說話方式、他的個性、他的喜好?
我在劇本裡面的線索找到的:我自以為是一個登山者、一個受過日本教育的人、可能是頑固的,在老年的時候可能是剛硬的?
直到我接收到如芳給我的錄音檔,我聽到那子孫中的對話,我開始去設想:是不是方慶綿其實是一個很開朗的人?
我抱持這樣的想像,再一次看他的攝影作品的時候,我一直在想著如何要把自己變成他?但我只能找到他的一張照片,一張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面容的照片。於是我又開始想像:他會是一個很豪邁的人嗎?但他拍攝過的那麼多作品來看,會不會他應該是一個很纖細的人?可是他又受了日本教育,以及那麼嚴格的師徒教訓,他在六十幾歲的時候到底會是怎麼樣去回憶他的過去?
他到底是誰?
我好想知道一個沒有受到歷史波及的人,一個沒有在白色恐怖的名單下面出現的人,一個很有可能跟白色恐怖的死亡照片有關係的人。
他到底是誰?
然後我聽著如芳給我很珍貴的錄音檔案,我只能從他的兒子的笑聲,開朗著談著過去的事情,在提起國民黨的時候,又是那麼明白著自己的立場,想像他是不是也是這樣的人?
我一直一直找不到誰是方慶綿,我一直一直想要接近他,一直想要知道他是怎麼說話的,一直想要知道他是怎麼努力的,一直想要知道它到底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嗎?
是因為岡本,或者是因為自己想要達成的目標,或者到底為什麼他可以就這樣翻越高山、看到雲海拍下那些照片?
而,如果是真的,他是哪裡來的勇氣去拍下一個被槍殺的屍體?
我好想知道在他心中,他是怎麼樣去看待自己的兒子因為聽了一首音樂引來了無妄之災?他是怎麼安全渡過這些難關?
接觸到〈春之佐保姬〉這首歌之後,我幾乎每天都在唱這首歌。我在洗澡的時候,一直模仿著如果是方慶綿他會怎麼唱這首歌?然後每次我躺在浴缸不斷重複唱這首歌時,我就一直流眼淚一直流眼淚,但很遺憾的是,我漸漸發現我流眼淚的原因不是方慶綿,而是高一生。
這讓我有點不知所措,因為我明明是想要知道誰是方慶綿!
如果之前那個表格問我,我要問編劇的問題是什麼,我其實對編劇,或者說這個劇本,沒有太多問題。
我只是很想要知道方慶綿是誰!
他是一個開朗的人嗎?
他是一個頑固的人嗎?
他恨日本人嗎?他恨國民黨嗎?他覺得自己是誰?
他一生追求的是什麼?他的腔調是什麼?
他離鄉背井的原因是什麼?
他愛他妻子的哪個地方?他是怎麼愛她兒子的?
他是怎麼看玉山的?他是怎麼看阿里山的?他是怎麼活著?
他是怎麼活過的?
我想知道他是怎麼死的,然後我才可以告訴觀眾,他是怎麼活的。
這是我身為一個演員的問題。

《藏畫》劇照 攝影/陳又維
文/施如芳
20230307
文尹:
這是我寫劇本這麼多年以來,第一次獲得演員從劇本有感而發出來的長信,太珍貴了,我會永久保存。
首先我要說,「發現」方慶綿可能做過的事,是我2020年底重啟藏畫的關鍵之一(另一關鍵是我看見遺照裡的張捷)。其實在我前面完成的版本當中,我早就興趣勃勃地寫過幾次遺照攝影師,因為毫無相關線索,其中一版,我大膽假設他是一個在事發當時,剛好來到嘉義經過陳家的年輕人,多年後他重返嘉義陳家,已是中央社的攝影記者。我說自己「大膽」,卻不敢想像(或相信)冒這麼大風險的人會是嘉義人,陳澄波的故舊,一個世故的中年人,開店做生意的人,要知道啊,當時的氣氛肅殺到連陳澄波的藝術知交拜把兄弟(張李德和)都不敢借擔架給陳家,以致張捷必須拆門板去把丈夫抬回來。
方慶綿到底是不是遺照攝影師?張捷、方慶綿生前都沒透露,至今身為長子的方重雄不願證實此事(他的記憶中當時二二八太恐怖,三月初他們家就跑去秀水避風頭),但攝影家李旭彬根據玻璃底片,從社會科學性的角度提出「是方慶綿」的這個可能。
「方慶綿」的出現讓我加倍地想完成《藏畫》。
原因是,我從這個人身上看到一個時代,他不僅僅是走過60幾年寒暑的個人,更是時代的象徵——「受日式教育、戰後必須否定從前一切」,背負失語傷痛的人。
所以文尹,你要演出的是這個人,更是那個時代。
方慶綿從小長於山區,長時間工作於山區。當時山區住很多日本人(不管是工人或主管),日本人是統治者,更是懂山的民族,他們把台灣的山當寶藏一樣開挖的同時,也帶來崇敬山與樹的哲學/生命態度。尤其方慶綿老老實實拜了一個出身武士世家的臼井老師,學了賴以維生、成就專業驕傲的攝影技術,他受到日式教育的影響之深,可想而知。
我從還沒讀到這麼多資料之前,基於戲劇性,就切分陳澄波和方慶綿的差別。兩人同樣受過日本教育,陳澄波甚至後來去日本留學,但陳澄波是漢人秀才之子,長方慶綿十餘歲,我相信他既吸收日本帶來的新知,骨子裡的信念仍認同自己是漢民族。方慶綿沒這麼複雜。穿日本服對他很自然,他賺錢買的店面就在日本人較多的大通,街上的孩子聽到方慶綿講台語,會很驚訝新高伯居然會講台語。所以我判斷,方的日本化程度高於陳澄波,內在認同也比較沒有像陳澄波這麼掙扎。
方慶綿對ECHO雜誌說出對臼井愛恨交織的情緒,我覺得一半真一半假。師徒輩分,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,加上青少年氣盛,這股被壓著的氣肯定是有的。但面對講國語的年輕人,他放大了這股氣。這是他習慣成自然的「假」。
我兩次訪方重雄,他都提及臼井要被遣返前,方慶綿跑去找他,師徒兩人在台中公園相擁展笑顏的合照。方重雄會惦記此事(有照片為證),想必方慶綿生前常碎念此事。而ECHO訪問在多年之後,報導會偏重臼井嚴厲的一面來寫就耐人尋味了。
以上是較真的史實探究。但我相信,放眼時代,與方慶綿有過相似學經歷,一整代倖存的台灣人,後來活下來的狀態大致都會是這樣。
所以文尹一定要惦記,你演的是一個時代的高度象徵。
方慶綿身上最華麗的標記,是他的職業和愛好。台灣島看起來這麼小,超過3000公尺的山有兩百六十多座,山的皺褶,讓台灣擁有宇宙級的豐富生態。方慶綿這個小小的個人,長年在玉山、阿里山走著,這兩座山是嘉義背靠的祖山,更是台灣的聖山。
方慶綿一出現,背後隱隱顯影的就是台灣的高山。
我曾經寫過一段張捷看著方慶綿拍的高山照片說出來的話:
「近近是樹,遠遠是山,清冷開闊的山頂,不是雲,就是霧,長年行佇大自然的世界,莫怪、莫怪,大樹的氣脈、大山的精神,恬恬駐在攝影師的體內!等轉來到山腳,家家戶戶,燈火閃爍,也度日,也度年,人間景象,燒熱又擱齷齪(ak-tsak),哪通予你揹到重院院?抵當時天會光,銃空(彈孔)收嘴(癒合)袂擱流血?一人一家代,底片請你交予我。」
請文尹想想,方慶綿長時間處於前後沒有人,隨時風雲變色會有生命危險的高山上,他是能忍受孤獨、甚至能享受孤獨的人!大自然對方慶綿的潛移默化一定很大,這樣的一個人,突然回到嘉義市區,會不會有天差地別、恍如隔世的感覺?!
面對殘暴瘋狂殺台灣菁英的二二八,方慶綿一定會怕!當眾槍殺參議員,在嘉義已經是第三波了,所以「方家提前逃往秀水」絕對可信,但有沒有可能方慶綿自己留下來,畢竟他是有特殊技能的人,他直覺自己能做點甚麼事(台北的鄧南光也拍過二二八,但這些底片後來都銷毀了)。但也或許他跟家人去到秀水,但後來他偷偷跑回嘉義。只要一個晚上,一個月黑風高的沒有路燈的宵禁夜晚,他就足以完成陳澄波的遺照。
但我願意展示方慶綿脆弱的一面,想到自己還有妻小要養,他會怕,真的會怕,所以我讓他在最後一刻曾經想退縮,是張捷叫住了他,這個她其實並不太熟的Camera先生。
不同年齡面對同樣的處境,會有不同的體驗和感受。我設定劇中的老方慶綿,是來到生命盡頭的狀態,回想前塵往事——當然他明意識不知道,但他的大我(或說高靈)多少略有感知,所以特別滄桑。
這一點也走在史實上。ECHO受訪是他人生唯一一次被專題報導,雜誌出刊一年後他就過世了。
以上,是我對「方慶綿」這個人與時代象徵的構想,供文尹參考。
還有一個更「高」的視角,文尹也可以體會看看:
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。莫說只有陳澄波冥偶,劇中其他三位現在也(早就)不在人世了。歷史幽靈回看彼此互為「點景人物」的人生,也是你可以嘗試看看的詮釋。
這封信我也同時傳給佩玉導演。